写本的「新」
书写在楮纸上的草体字紧迫而来,强调着自己的古文书身份,浓重的气味扑鼻而至——在每次触摸古文书时,喜于相逢的同时,都会产生出能够直接接触古文书的感谢与敬畏的心情。有不能辨认的文字,有无署名和收件人地址的文书,也有难懂的内容。但是,文书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面前,面对现在提示着自己过去的存在。
在财团法人藤井永观文库中,收藏有很多圣教、古文书的写(即缮本)。所谓写,是指用手抄写书(文书)而成的抄写本,它被称为写(写本)。特别是在抄写圣教的情况下,书写人常常会把何时何故抄写何人之书等情况写在奥书(即书籍底页的记录)上。而所谓圣教(しょうぎょう),虽然是指佛祖的教诲,但广义上是指从老师处学到的秘说、佛典,以及在寺院社会生成的佛教相关之文书与典籍。
圣教的奥书里饱藏着书写年代、传来处、书写者、书写动机等等,涉及历代书写者的情报。奥书里所记载的历代书写记录(以下称书写历),是以本奥书(即最早的奥书,多为原本撰者的奥书)为起始的。即便是写本的文书内容相同,但离本奥书的书写年代越远,现存写本的成立年代就相对越新。一般来说文书越古越有价值,但是相对于原文书的成立年代,写本书写年代的「新」上,也有很大的意义。
文书拥有越多的书写历,就意味着在相当的时间里文书被很多人抄写的实事。因此,在内容的成立与写本的成立之间,产生出时代的距离。但是,这种时代的距离表明,其间作为有必要书写的文书所受到的一种重视。可以说,在各个时代(各书写年代)得到再生的文书,即写本存在本身,便意味着这文书处在「旬」(应时)的时代。
祖本的「古」
所谓祖本,是指众多传本的原本,即成为写本根据的著者亲自书写的书。在圣教的奥书里,有时会记载书写者对祖本或祖师的感情、动机等。
展览会展出的NO.7『九曜秘暦』的奥书如下。「本云、平治元年九月六日書了、興然/応永三年七月日以二理明房自筆本一、/令二模写一了、件写本依二祖師真迹一、令/レ寄二進慈尊院経蔵一了、/法印権僧正賢宝六十四」
此奥书中,有两位与正文内容有关的僧侣登场。也就是说,平治元年(1157)兴然「书写」下祖本,应永三年(1396)贤宝「模写」理明房兴然的手书本,并且将兴然的手书本捐献给劝修寺慈尊院的经楼。如解说文所述,兴然是劝修寺慈尊院流的祖师,贤宝是东寺观智院第二代院主。奥书里写道,因为贤宝模写的是「祖师真迹」,所以事后将真迹捐献给劝修寺慈尊院经楼。
贤宝所在的东寺观智院的传法脉系,与劝修寺慈尊院相关联。因此,从平治元年至贤宝书写时的应永三年,兴然的手书本传到了东寺观智院。其间相距二三七年。其后,作为祖本的兴然手书本藏于劝修寺经楼,而贤宝所模写的写本则藏于东寺观智院。以上情况是根据奥书而得以明确的。
贤宝从「祖师真迹」中找到的对祖本的认识,既体现出对祖师兴然的敬意,也体现出「真迹」本身所拥有的超越的价值。比起贤宝亲自「模写」的写本来说,兴然的「真迹」所具有的祖本的「古」,则是再次产生出来的价值。贤宝的「模写」并不是单纯地将书看作抄写的对象。对祖师兴然和自己所属之慈尊院流的感情的分量,促使贤宝成为一名书写者。于是,东寺观智院和劝修寺慈尊院,各自所拥有的成为姐妹的兴然本『九曜秘暦』,作为连接真言密教法流的纽带,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
作为有着历经岁月之含义的文化遗产的「古」,与抄写前成立的祖本的「古」,虽然同样是古,却有着不同的意思。而且它们也绝不可能相同。
写本的生成
一册写本至成立为止,有着怎样的过程呢?如果是图像集,到完成为止会有不少人物参与其中。
下面出示的是NO.4『曼荼羅集』的奥书。「図画本云、/今此抄三巻、先師理明房阿闍梨興然往年雖/集レ之、諸尊色像未レ図レ之、且守二彼遺命一且/為レ散二象(衆)霧一、仰二両三之画云(工 )一、図二諸尊之/形像一而巳、有二所違一者後覧添二削之一、/権大僧都光宝/天福元年十月之比、年来所持本/書二制図像一畢、定真本也、/此抄三帖依二師命一書レ之、油紙図像同写レ之、/大法師隆聖廿三歳九臈 /此集三帖頗希也、尤可レ為二秘蔵一焉、/弟子僧覚恵即応レ励二志修補経/営一訖、後葉勿二容易一、且不レ可レ許二他見一矣、/延享第五戌辰歳五月十八日/ )一、図二諸尊之/形像一而巳、有二所違一者後覧添二削之一、/権大僧都光宝/天福元年十月之比、年来所持本/書二制図像一畢、定真本也、/此抄三帖依二師命一書レ之、油紙図像同写レ之、/大法師隆聖廿三歳九臈 /此集三帖頗希也、尤可レ為二秘蔵一焉、/弟子僧覚恵即応レ励二志修補経/営一訖、後葉勿二容易一、且不レ可レ許二他見一矣、/延享第五戌辰歳五月十八日/ 定額僧貫首勧修寺浄土院僧正賢賀世寿六十五法臈五十六」。 定額僧貫首勧修寺浄土院僧正賢賀世寿六十五法臈五十六」。
在此奥书中,总共有六个人登场。他们是撰者的兴然·光宝·定真·隆圣·觉惠(1604—?)·贤贺(1684—1769)。兴然收集了成为本书依据的曼荼罗,光宝整理兴然收集的曼荼罗且绘制诸尊形象,定真模写图像,隆圣将图像模写到油纸上,秘藏及修补经营本书的是仁和寺真光院的僧觉惠和东寺观智院第十三代僧贤贺。
如此,一册图像集的成立需要经过许多人的手。本书被制作的原动力中,既有「遗命」「师命」等针对祖师的忠诚和义务,也有对本书抱有的「颇希」之价值观,还有「秘藏」「勿容易」「不可他见」等接触本书的方式。这样的认识是阶段式形成的,并不是成立当初一气呵成的。本书的三帖形成于,随着岁月流逝而产生的价值,以及随着此价值而产生出来的尊重行为。这些也可以说是本书在质的完成上所必需的条件。
兴然着手收集曼荼罗的时期更要往前追溯。但是,从最初的奥书时期即天福元年(1233),到最后的奥书时期即延享五年(1748),本书保有了总共历经五一五年的奥书(历史)。奥书不单是弄清成立年代的证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暗示经历数次生成阶段的本书状况的历史叙述。
写本的产生是祖本得到重视的结果。内容饱含着穿越漫长历史的价值,而写本的存在又正好证明了这种价值的保有。作为文化遗产的古文书的「古」,与「新」写本的价值乍一看是相反的。但是作为文化遗产的「古」又恰好是其穿越漫长历史的证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古」与「新」同样保持着历史的生命力。
存在着很多的写,即便是「新」时代的写,其写本还是处于漫长的「旬」(应时)的时代之中。写本将祖本的价值传递给未来,同时承担着证明文化遗产之「古」的作用,犹如活着的见证人一般。
現在的活字
现在电脑普及,复印及粘贴也极为容易。但是却没有触摸纸张的手感,也没有不能辨认的字,以及让人能够感受到的时代的气味。从手写到打字机,再从打字机到电脑。说到文书,其存在已经是铅字,是媒体。
从文书的书写到修补,从宝物到文化遗产,现在更是朝着保全这些文物的方向迈进。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对以有形无形之文化遗产为首的原资料进行电子化存储处理。在不伤及文书的情况下,即可紧凑地阅览原件的同时,文书的手感、气息朝着数据的另一方远去——有幸得以与古文书相逢的感慨,这也许是因为自己生活在能够实际接触原文书的最后时期的缘故。古文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主张。正因为如此,面对被电脑画面吸收了的实物存在价值,比如文书自身又会做何思考呢?难道几百年都不能追加书写历吗?……等等。不用说,文书是沉默的。
但是现在的古文书,把平常的工作托付给电子画像,时而也会在展览会上展露其原文书的风采。写本的「旬」(应时),尽管改变了媒体,仍然将得到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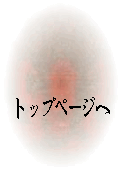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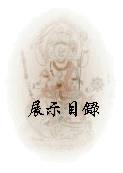
|